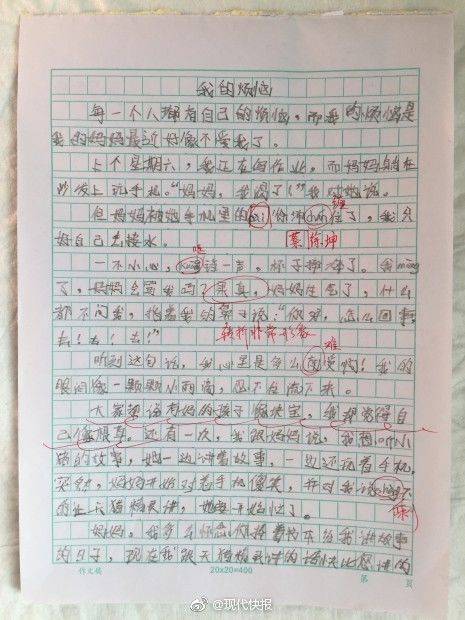立冬這天,一場大雪紛紛揚揚,下了一整天,雪有一拃多厚。暖氣還沒送,屋裏屋外又濕又冷。翻箱倒櫃找衣服,順便整理一下衣櫥。在一個花包袱裏又發現那件對襟小棉襖:紅綢碎花,訂著盤扣。
這是結婚時母親飛針走線為我縫製的嫁妝襖。母親說,紅到三十綠到老,當時還做了件綠花的和這件紅的是一對。紅襖綠襖,因為不時興,沒幾年就不穿了。衣櫥裏新衣進舊衣出,記不清送出去多少,唯獨這件小棉襖一直沒舍得。
年輕時,每到天冷母親就絮絮叨叨催促多穿一些,暖和。那時愛俏,對母親的勸告,表麵上答應下來,卻依舊我行我素。盡管母親做的棉襖既暖和又板正,可還是嫌穿上它鼓鼓囊囊不好看。那幾年,時興一種裏的毛衣,彩色的絨線編織出美麗的圖案,穿在身上大方得體,很洋氣。後來鴨絨襖,駝絨褲,以及輕便的羊絨衫漸成新歡,老棉襖就壓在了箱底。每年夏天,日頭好的時候拿出來曬曬,就又放回去。
多年後,在街邊擺了個小攤賣羊肉,那個冬天似乎格外冷,盡管像包粽子似的把自己一層層裹嚴實,隻露出兩隻眼睛,寒風卻還是會突出重圍,肆意襲擊我,仿佛要劫走身上所有的暖。立在冰天雪地裏,又想起箱底那件棉衣。找來穿上,老棉襖的溫暖悄無聲息地將我包圍。十層單不如一層棉,這話不假。
母親也有一件布棉襖。那年初春,父親走了,八十歲的母親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。我們姐妹幾人小心翼翼地陪著母親,順帶整理父親的遺物時,才發現母親那件棉襖。仔細翻看,表皮已經褪色,棉絮兒也有些發黃,想想整日操勞的母親竟沒有一件可身的暖棉,不由心生愧疚。於是,悄悄地買來襖片棉花,頭一次學著做。明亮的燈影裏,柔軟的棉花積蓄著陽光的溫情傳到膝上,脈脈流到心裏。不覺想起小時候,母親坐在昏暗的燈光下,為我們一針一線縫衣服,納鞋底的情景。母親手中的針線,縫補著那些清貧的歲月,不知濾盡了多少孤單和辛苦,使我們得以佑護,感到溫暖。那時,母親已經花眼,用完一根線,常常左手舉針右手拿線,仰頭,靠近燈前紉針。有時紉不上,就叫我幫她。紉上針,母親繼續手裏的活計,不時轉過頭看看在燈下做功課的我。對我說;初一紮針十五拔,強起求人家。少時不解此言,真正懂這句話,是在嚐了很多苦楚以後。很多事,不怕做不好,隻要肯自力更生用心做,就會幹成。
做好棉衣,抽空送去。雖是做成開身的樣式,也還費了些勁才給母親穿上。夕陽從窗戶斜進來,母親佝僂著背,坐在椅子上,低頭摩挲著衣角喃喃自語:“俺這小閨女長大了,手也巧了”。站在母親身邊的我,正給她梳理額前的亂發,聽到這話,不覺眼角濕潤。揚揚頭,悄悄把那些渾濁的東西流回心裏。一時暗自喟然:就我這活路,根本拿不出手,僅僅是不露棉花而已!哪是我的手變巧,分明是母親老了,母親老的連針線也拿不動,再也縫不起那些細碎的日子!那天,我第一次端了熱水,蹲下身,給母親洗腳,母親怯怯的,有些不好意思。撫摸著母親纏過的小腳,淚水一再漫上心頭。
有一次和朋友吃飯,看著朋友的閨女纏繞在側的幸福,又想起小時跟在母親身邊,老輩人說的話,“菠菜疙瘩芫荽梗,老生閨女是一景”。我與母親相差四十歲,是不折不扣的老生閨女。我把菠菜疙瘩芫荽梗,老生閨女是一景打趣地說與朋友聽,六七歲的孩子懵懂可愛,嬌嗔地對我說“阿姨,我不是菠菜疙瘩,我是媽媽的小棉襖”。大家撫掌而笑。看著天真的孩子,我也笑了,隻是心頭卻湧起一些莫名的甜蜜與酸楚:
小時候我也像眼前的孩子一樣愛撒嬌。冬天,大娘家的姐姐來找我玩,我還賴在被窩裏不起,問姐姐外麵冷不冷。母親望著窗外嚇唬我:咋不冷,今早上去關口拾大糞的韓三耳朵都凍掉了。邊說,邊把棉衣放在煙囪上捂熱遞給我。有一年冬,頭天夜裏母親還坐在炕頭上給我做棉襖,早上,肚子就疼得起不來床,滿頭是汗。村裏的赤腳醫生用盡渾身解數也沒招。那時,大姐二姐還有父親都上坡了,看著母親痛苦的樣子,我和三姐手足無措,嚶嚶哭泣。母親也哭,說,這倆小閨女,兩隻手還打不起個圓圓捧來,麵條還撈不到碗裏,咋辦呀。最後,隊裏派人開拖拉機把母親送到醫院,才救過來。後來知道,母親得的是膽道蛔蟲,在那時很危險,現在,這種病很少見了。
前些天,戴著老花鏡給小孫子做棉衣,小孫子騎著扭扭車在屋裏跑來跑去,玩了一會兒,興致漸無,放下車子,噘著嘴靠在我身上:
“奶奶我想媽媽了”。
“然然,媽媽下班就回來,奶奶和你一起等,好不好?”耐心安慰。
然然望住我:“奶奶,你想你的媽媽嗎?”
我把小孫子攬在懷裏,默然想起一些過往:那年夏天,二姐去武漢和親家見麵,我和三姐負責照顧母親。那時母親已是八十六歲,舉手投足諸多不便。時值酷夏,高溫難耐。夜裏,三姐睡另一張單人床,我就橫睡在母親床尾。睡夢裏忽覺一陣涼風,也有其他響動,慌忙起身,原來是母親在給我扇扇子!
母親去世前一天晚上,基本沒有吃東西,我們感覺不太好,忙給在濟南的二姐打了電話。第二天中午二姐抱著不足一歲的孫子回來時,母親還高興地牽了牽孩子稚嫩的小手,示意家人抱開他,又摸了摸姐姐的衣服,說,這麽冷的天,也不知道穿厚點,圍上圍巾。在全家人的守護下,母親像一朵清淨香潔的蓮花,離開了我們。
小孫子睡下,我又拿起未做完的棉衣,一根線用完,窗前紉針。可是,右手的細線,卻怎麽也穿不過左手清晰的針眼!
編輯:文峰山人
本文到此結束,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